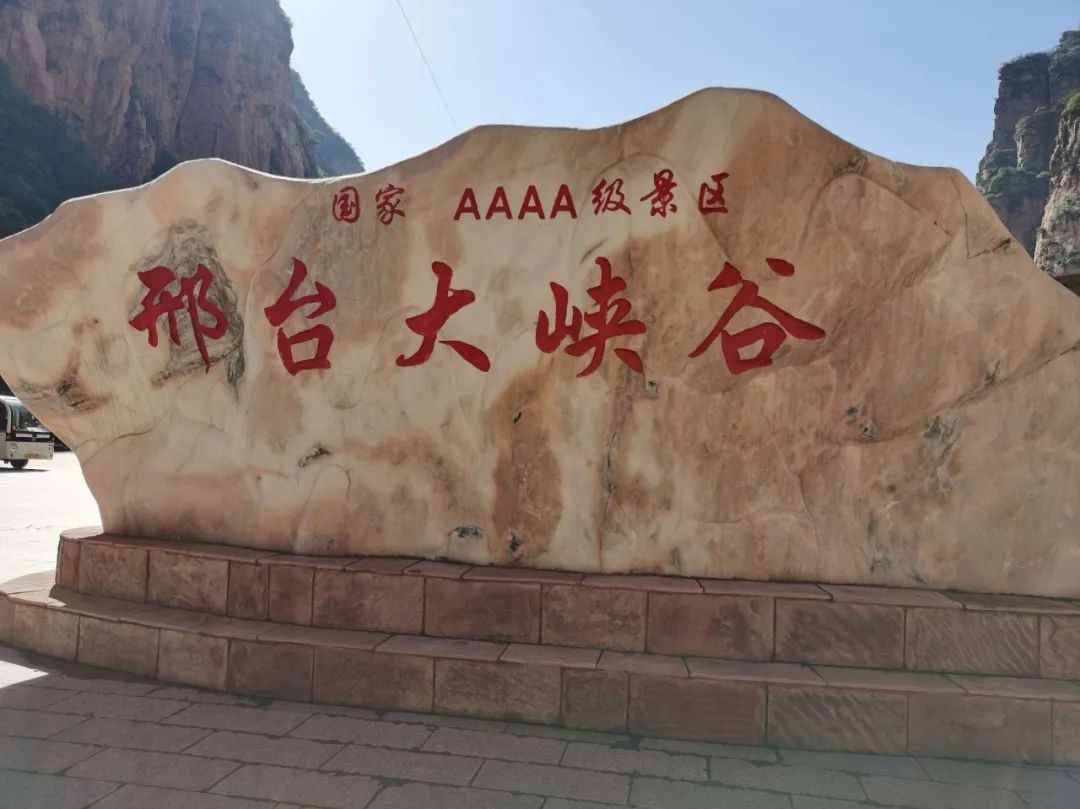近日,我的阅读沉浸于两位本土作家的一部长篇小说里。我先被其恢弘巨制,皇皇部头而震惊,后又被其跌宕故事、生动笔触和情感细节不断打动。
张金良、刘英民,这两位出生于太行山下的沙河市写作者,前者有些陌生,后者可是太熟悉了,他曾兼任市文联的党组书记、市委宣传部的原副部长。他俩在历经近十五年的雕琢打磨之后,《远乡》(三部曲)之《山遥水遥乡梦遥》《花红火红高粱红》《街风巷风花信风》,终于2024年8月由天津出版传媒集团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。这是邢台文坛近年来少见的令人眼前一亮的厚重之作。
山乡村野映照轮回日月,庄稼男女印证世事更迭。
三部曲的故事上溯清末,下至上世纪后期,并踔厉走向新时代。百余年的时间跨度,百余位人物的沉浮荣辱,聚焦于太行山麓的山乡古镇大坡地村。其恢宏的历史画面,灵动的人物形象,跌宕的故事情节,深刻的主题寓意,鲜活的乡音乡语,全景式展现了中国农村在历史巨变中的壮阔行程。作者把20世纪的百年岁月如倒回胶片似的重新播映了一遍。庄稼百姓踏响二十四节气的每一个足音,都让人身临其境一般,可以目睹并触摸到去而复返的“逝者如斯”。其中的百感交集,也正如书中所述,“老牛暮归,踏碎了遍野夕阳”。掩卷长思,由“惊”而“撼”。
匠心独运,妙笔传神
故事主角之一魏老大,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,为了活命,如花少年变成了财主家的小杂役。因为误看了不该看的,不仅被财主死命抽打,还要他说说“心肝肺咋长到了脚后跟”。
新社会到来之后,他不仅分到了能够活命的土地,还和财主东家成了连襟。新中国的第一个麦收之后,这位自小勤劳的庄稼汉,才终于收获了第一捧属于自己的粮食!他扯了两碗锄板厚的“拽面”,像两碗“卷卷曲曲的泥鳅”。他端着这碗“泥鳅”,第一次坐到石碾街的大槐树下,吃了平生第一顿体体面面的饭,终于知道了“活人,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!”
他的一生,被上下不通畅的怪病憋住过五次。第一次是他娘被饥饿和病痛折磨至死;第二次是分了房、分了地之后,财主的儿媳妇给他拆洗缝补好了破被褥;第三次是他的老财主连襟警告他,“好闺女哪个也出不了村,丈母娘那边的好男人没死绝”;第四次是因为他拿性命换来的半亩“大坡地”要被收回;第五次是数十年后,他的半亩“大坡地”终于被开垦成了四亩多,却被他的老东家、他的连襟亲戚,也即边家的煤矿蚕食侵吞无法耕种,他被一口气憋住再没有缓过来。气绝之时,院子里的锄头扁担被一起撞响,他的妻子惊叫:“快撵恁爹,快给恁爹叫魂儿!他扛着做活儿的家具,去鸡冠山种地了!”
魏老大披挂着黑白无常索命的镣铐,在即将跨过奈何桥的最后一瞬,也要去他的“大坡地”把尚未完毕的农活做完!
中国农民对黄土地的热爱和执着,是镌刻在骨子里的。尽管故事把这个情节化实为虚,但艺术化处理更能入木三分,艺术语言更加力透纸背。——黄土地,不仅是庄稼百姓的生命,更是这个社会的立世根基。
可是,魏老大的生命终结后,按照遗愿埋到了他鸡冠山的“大坡地”。谁料想,他灵魂尚未走远的遗骨,突然被边家煤矿轰然坍塌的矸石山,莫名其妙地又埋葬了一次!令人心酸的是,数十年前他半夜偷偷耕种王家花园里的地,一个俊俏的幽灵在梦里给他说:“你这么好个人,给你个啥?没啥给,那就叫你埋两回吧!”——人不惜,鬼不怜,这岂不就是庄稼汉的宿命?
形象鲜明,逸趣横生
《远乡》(三部曲)均是由个性形象鲜明而突出的人物引发出若干逸趣横生的故事,并且通过对这些故事的精心构造,使人物形象更具鲜明特点且活灵活现,极具辨识度。通过对典型人物的塑造,和读者形成共振共鸣,张力十足,代入感强劲。
20世纪早期那个年代,尤其是在偏远乡村,男女婚事几乎全靠媒婆撮合。不算太穷也算不上大富的周大中算计精明,要求婚娶之前必须先看女方一眼。媒婆无奈,告知他坐在巷子口最高处的女子就是。周大中跟在媒婆屁股后面,看见巷口最高的石墩上,坐着一位杏花女。他没有料到巷口的房顶上还坐着一位杏叶女。大喜过望的周大中终于盼到了大喜夜,才发现林妹妹换成了宝姐姐——心中的“杏花”变成了眼前的“杏叶”。
周大中急得不行,媒婆说:“谁哄你唻,俺给人家闺女找了个傻女婿!巷子口的石礅比房高?”
周大中就更急,媒婆又说:“咋不坐到石礅上?谁家闺女能坐到大街上,闲日摆着等你看?就是皇帝选秀女,还抬着小轿儿,去背旮旯里偷偷瞧呢,你比皇帝,差远了!”
媒婆知道了周大中的心思后,皱着眉头捂着肚子,她那个羞涩之地,不顾羞涩地大响了几声,撇着嘴弯下腰,把头扭到了一边去,身子还一颠一颠地颤,颤了一会儿后,一边笑着一边说着扭远了。“哎呀呀,哎呀呀,那个?那个?你也敢想?月亮里头还有一个天仙,你想不想?就靠恁家那一布袋麦子、一布袋米?哎呀呀,哎呀呀!要有那样的好事,还轮得上你?”
通篇读来,看不到对媒婆品行有半个字的正面描写,但一个软硬兼施、奸钻油滑的人物形象早已跃然纸上。
文学艺术的高妙之处就在于此。它本无颜色,却能让人看到赤橙黄绿;它没有声响,却能让人听到短歌长调;它不能行动,却能带人上天入地;它没有生命,却能把生灵万物、神仙老虎描绘得百态千姿。刻录在龟壳、竹片、丝帛、麻纸等等之上的点横撇捺,哪怕是远古的河流山川、云雾雨雪,只要永久地保留下来,千万年之后的后人照样可以读到悟到里面的故事,且历历在目,铭记于心。语言文字是小说的好“口舌”,好到最妙处,不须与君说。
胸纳万壑,太行花开
起初,我不太相信《远乡》(三部曲)历经近十五年之久。两位写作者均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,两人同村,年龄仅差一岁。若果真那样,就意味着他们自不惑之年起,冷板凳一直坐到了如今的年逾花甲。后来我掌握到的事实,均证明果真如此。
表演升华到艺术,肯定炉火纯青,演啥像啥;绘画升华到艺术,自能眼观千帆竞秀,泼墨百舸争流;舞台升华到艺术,更包含着“一分钟和十年功”的天道酬勤。以文字为载体的小说艺术亦是如此。
20世纪百余年的中国社会进程,可谓沧桑巨变、波澜壮阔。作者以文学形式,将这段开天辟地、承前启后的历史风云,还原为百万字的《远乡》(三部曲),将20世纪前期的百姓屈辱史、苦难史,和20世纪后期百姓的翻身史、变革史,凝结浓缩在太行山区的乡野古镇,并以此透视整个社会的壮阔进程,不仅需要精心的架构设计,更需要相当厚重的历史和社会知识做支撑。《远乡》(三部曲)饱含了两位作者十五年甚至更多时间对生活感悟的沉淀和累积,同时,也融入了两人在职场多年的磨砺和学习。在生活中,他俩同村同岁,情同手足;在创作中,他俩默契无比,天衣无缝。当他俩从执笔书写的那一刻,便做到了绣口随出,吐纳有致;胸有成竹,下笔如神。
《远乡》(三部曲)的正文前有一段题记:
太行花:古老的残遗物种,中国特有、太行山独有属种,生长在太行山的悬崖上,或者林内的岩石裸露和土层瘠薄处。不能大量采种,分布区域狭窄且范围日益缩减,不采取有效保护措施,将濒临灭绝。
细细思索之后会发现,作者把太行花作为三部曲的故事暗线贯穿始终,是把这种稀有草本植物暗喻为中国百姓、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优秀品质。其中有担忧,有祈盼的含义,更有展望和颂赞的意味。
如今,中华民族在自己的文明发祥地繁衍发展五千年,在世界民族之林不仅首屈一指,而且绝无仅有。其拓印在世界历史上的每一个足印,尽管深浅不一、沉重艰难,但都是扎扎实实、端端正正。
从《远乡》(三部曲)里,读到了百姓坚韧和豁达情怀,读到了乡村历史和命运变幻,读出了民族奋争和自强精神。